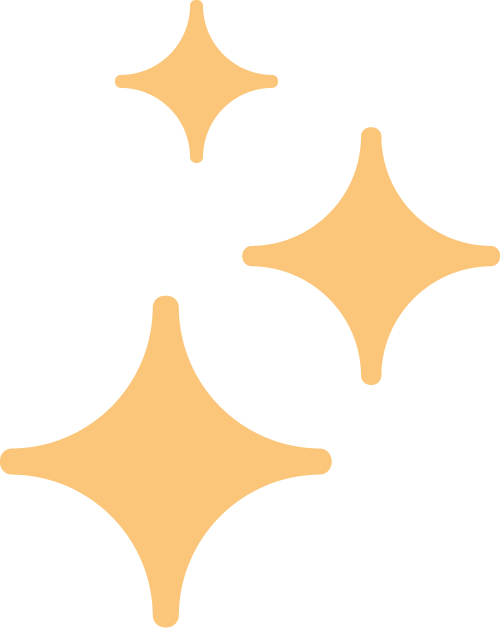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2018 年成立的天津爱思达深耕航天碳纤维复合材料,构建国内最完整整流罩型谱且技术达国际先进,完成多轮融资及 IPO 辅导备案,部分产品批产。

近日,2019 年成立的江苏天兵航天公示 IPO 辅导一期报告,中信建投任辅导机构,主营运载火箭等航天业务,康永来持股 26.5%。

NASA 与美国能源部签署备忘录深化合作,研发裂变表面动力系统,计划 2030 年前部署月球反应堆,支撑探月及火星任务。